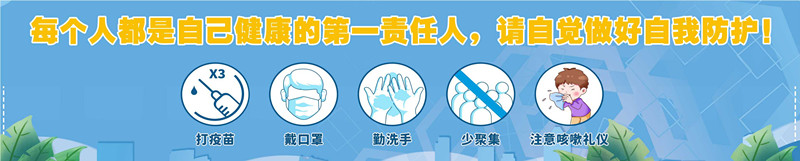东边的山头,刚刚露出鱼肚白,树上的鸟儿,唱起了山歌,山乡就这样醒了。
不知不觉间,袅袅炊烟,从一处处农家屋顶升起,缭绕着,盘旋着,然后飘向山峦间。而后,吃罢早饭的村民,走出家门,或是扛着,或是背着农具,到了地里,开始了一天的农活。
我的老家,在谷城南河镇山乡。19岁以前,我在老家干过四年农活。山乡的农活,多种多样。随着农时变化,农活也随之变换,今天是薅草,明天也许是挑收割的庄稼。
古人曾说过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这首诗朗朗上口,通俗易懂,相信很多人都会背,可是很多人未必有过锄禾的艰辛。
锄,我老家人统称锄头。锄头有两种,一种是薅锄,一种是挖锄。薅锄薅草,挖锄挖地。古人说的“锄禾”,在我老家就是薅草,也就是薅掉庄稼地里的杂草。
我在干农活时,还没听说过“化学除草”。庄稼地里长了草,全靠人来薅。要是不薅,杂草就会比庄稼长得快,就要和庄稼抢肥吃。冬季和春上要薅麦草,夏天要薅苞谷草。像苞谷苗、麦苗,一旦起身长高了,就不用再薅草了。这时的庄稼就会遮住野草,野草得不到露水和阳光,自己就会死掉。
老家人用的薅锄,安有一根长长的握得住的木把,木把一头安着铁弯钩,铁弯钩又安在铁锄片上,这就是薅锄。
薅草,是人辛苦、受累的农活。比如,三伏天里薅苞谷草,天上大太阳抵着晒,地面也被太阳晒得像蒸笼,人朝太阳底下一走,仿佛就能看到忽闪忽闪的火苗子。这时在苞谷地里薅草,真是酷热难耐,浑身流汗。天上太阳晒,地上热气蒸,人还要弓着腰,双手攥着薅锄把,低着头使劲薅着草。土地被太阳晒得干焦焦的,再加上地里石头磕磕碰碰,每薅一锄草,都要下大力气。如果稍不注意,锯齿般的苞谷叶子,就会把脸和眼睛划伤,汗水一浸,疼痛难忍。像这样干不到一会儿,人就要喘着粗气,浑身都是汗淋淋的。汗水从额头、脸上、颈脖不断往下流,一直顺着腿流到地上,你说这是不是“汗滴禾下土”?
有一次在薅苞谷草时,我对父亲说:“太阳这么大,为啥非要在太阳底下薅草呢?不能干别的活吗?”
父亲说:“太阳大,草才死得快,死得干净。”
我虽然明白了,可还是叹了口气,说:“人,就是一个遭罪的命。”
“人来到世上,就是受罪来的。”父亲说,“天底下哪有尽享福的好事?”父亲虽然不会说“不劳而获”这个词,可他这话里,不就包含着这层意思吗?
我没再说什么,心里像一盆子清水一样明澈,只好又弓起腰低下头,继续薅草。
在我身旁薅草的村民司念寿,朝握薅锄把的手心吐了一口唾沫,搓了搓,边薅边说:“古人不是说过‘辛苦做,快活吃’嘛!”
大家薅了两个时辰开始休息,老家人叫“歇气”。这时,人们纷纷从苞谷地里钻出来,走到树荫下,年轻人或坐或躺,岁数大的男人们吸着旱烟锅……虽说大家都很累,但往树荫下一坐,又说笑起来了。这种劳动间隙的热闹,赶走了疲劳,再薅起草来,格外有劲。
现在的老家人,干农活都是一家一户了,不再像往年大集体人多。虽说是单家独户,主要还是夫妻两口子在干。两口子薅草,累了也会坐到树荫下歇气。这时的男人,会从放在地边的大土茶壶里,倒一碗淡黄色的大叶子凉茶,递给自己的女人。女人喝了,既解渴,又享受着丈夫浓浓的爱。
这种在汗水中浸泡的爱,这种在烈日炙烤下的爱,这种在日出而作中的爱,不正是人间的一种幸福和甜蜜吗?
说罢了农活“薅”,再说“挑”。
“挑”这种农活,在山区更是重体力活。因为在坡上,在地里,背和扛都比不上挑。只有挑才能把收割的庄稼,又多又快地运回来。
在山区能不能挑担子,是小伙子长没长大的重要标志。一个小伙子,只要能挑担子了,那在人们眼里就成人了。
在老家干农活时,我就挑过粪,挑过蒿,挑过红薯,挑过麦捆子,挑过稻谷捆子,挑过苞谷坨子,挑过柴,修堰塘时还挑过泥巴……
说挑是重体力活,这可不假。一副挑子,只要挑上肩,每时每刻就得用身子骨支撑着。木头扁担磨着肩头上的骨头,即使咬着牙,也是难以忍受的。
从山里出来的人,没有人没挑过担子。一个干农活的庄稼汉子,挑没挑过担子,就看他的肩膀头斜不斜。人们大都喜欢用右肩挑担子,常挑担子的人,走路时右肩膀习惯性地要比左肩低,这就是长期挑担子压成的习惯,也是一年四季的劳迹。凡是遇到这样的人,那准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,一个能负重前行的人。因此,挑担子,是山乡男人养家糊口的基本功。
挑,在农活中无处不在。入冬后,要把沤了一个夏天的猪牛粪等农家肥,挑上山种麦子用。一开春,又要把沤了一冬的猪牛粪,挑上山点苞谷用。湿坨坨的农家肥,装满两筐子,少说也有一二百斤。力气小的人,真是挑不动。
崎岖的山路,不是上就是下。挑着粪上坡,要防止前面筐子的粪洒到自己胸上、后面筐子的粪掉在路上。下坡时,又要防止后面筐子的粪洒到自己背上、前面筐子的粪掉在路上。
我那时力气小,一次只能挑七八十斤。就这样,一挑粪挑到地里,路近一点的话,我要歇两次。路要是远了,就得歇三次。我看到长年累月干农活的村民们能挑一二百斤,无论是上坡下坡,沿途都不歇气,右肩挑累了,就麻利地换到左肩上挑,我是羡慕极了。
到了夏季,山上的麦子全都黄了,就要收割。割麦子虽不累,可是挑麦子却累人。两捆麦子,挑在肩上,步步山路,上坡下坡都很吃力。一面坡的麦子还没挑完,人就累得瘫坐在地上,懒得动弹。可想到那一捆捆麦子,都是自己汗水换来的,想到那又香又白的麦面馍馍,人也就来了精气神,有了劲头,扛着扦担一次次走上山坡,直到麦捆子挑完为止。
秋天,是稻谷成熟的季节。田野的风,吹拂着一畈畈金黄的稻穗,稻香扑鼻。
收割的稻谷,不像麦子那样干燥。麦子成熟后,麦秆是干的,挑着轻省。而稻谷成熟后,稻谷秆还是湿漉漉的,挑着两捆稻谷捆子,越挑越重。更难的是,挑稻谷捆子在田埂上走,稍不注意,脚下一滑,人和稻谷捆子就会滚到田里。
收割稻谷,虽然活很累,但看到风吹一浪一浪的稻穗,好像是在向庄稼人频频点头,那到手的粮食还没进场,要把丰收的果实颗粒归仓,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,心里也是甜美的。
山乡农活有很多,唯有薅和挑,是最累人的。正是累,庄稼才会长得好。正是累,夏秋才有好收成。正是累,家家才会粮满仓。正是累,农民才能把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。
作者:帅瑜
来源:谷城县融媒体中心
编辑:邓植元|审核:余运超 琚晓青